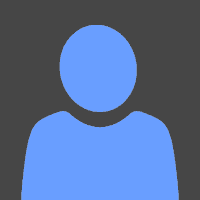阿特米西娅·詹蒂莱斯基
Artemisia Gentileschi
代表作品:
艺术家名:阿特米西娅·詹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
生卒日期: 1593年7月8日 - 大约1652年
国籍:意大利
阿特米西娅·詹蒂莱斯基的全部作品(76)
阿特米西娅·詹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Artemisia Lomi),又译为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意大利巴洛克画家。詹蒂莱斯基被认为是17世纪最有成就的艺术家之一,最初以卡拉瓦乔的风格工作。她十五岁时就开始从事专业工作。在一个女性几乎没有机会接受艺术培训或从事专业艺术家工作的时代,真蒂莱斯基是第一位成为佛罗伦萨“艺术学院”成员的女性,她拥有国际客户。
詹蒂莱斯基的许多画作都描绘了神话、寓言和圣经中的女性,包括受害者、自杀者和战士。她的一些最著名的主题是《苏撒拿与长老》、《朱迪思斩首霍洛弗内斯(乌菲齐)》,以及《朱迪思和她的女仆与赫洛弗尼斯的头颅》。
詹蒂莱斯基以能够以极大的自然主义描绘女性形象而闻名,并以其处理色彩以表达维度和戏剧性的技巧而闻名。
阿戈斯蒂诺·塔西(Agostino Tassi)年轻时强奸她的故事以及她参与对强奸犯的审判,使她作为艺术家的成就长期蒙上阴影。多年来,詹蒂莱斯基一直被视为一个好奇的人,但她的生活和艺术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受到了学者们的重新审视。她现在被认为是她这一代人中最进步、最富有表现力的画家之一,在伦敦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等国际知名美术机构举办的大型展览充分证明了她的才华。
传记
早年生活
阿特米西娅(Artemisia Lomi Gentileschi)于1593年7月8日出生于罗马,尽管她的出生证明表明她出生于1590年。她是普鲁登齐亚·迪奥塔维亚诺·蒙托尼(Prudenzia di Ottaviano Montoni)和托斯卡纳画家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的长女。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是来自比萨的画家。到达罗马后,他的绘画达到了表现力的巅峰,灵感来自卡拉瓦乔的创新,他从中养成了画真实模特的习惯,没有将模型理想化或美化,事实上,也没有将其改造成一部强有力的现实主义戏剧。1605年,小阿特米西娅在卢西纳圣洛伦佐教堂出生两天后接受洗礼,成为母亲的孤儿。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她开始接触绘画:阿特米西娅是在她父亲的工作室里被介绍到绘画的,表现出比与她一起工作的兄弟们更多的热情和才华。她学会了绘画,如何混合颜色,以及如何作画。到1612年,当她还不到19岁时,她的父亲就可以夸耀她堪称楷模的才华,声称在她已经从事了三年的绘画职业中,她是无与伦比的。
在那个时期,她父亲的风格受到卡拉瓦乔的启发,所以她的风格也深受他的影响。然而,阿特米西娅对主题的态度与她父亲不同。她的画很自然。奥拉齐奥的是理想化的。与此同时,阿特米西娅必须克服“传统态度和心理屈服于这种洗脑和对她明显天赋的嫉妒”。通过这样做,她的工作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和认可。
她现存的最早作品是17岁时的《苏撒拿与长老》。这幅画描绘了《圣经》中苏珊娜的故事。这幅画展示了阿特米西娅是如何吸收卡拉瓦乔的现实主义和效果的,而不是漠视安尼巴尔·卡拉奇的古典主义和巴洛克风格的博洛尼亚学派( Bolognese School)。
阿戈斯蒂诺·塔西强奸案
1611年,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与阿戈斯蒂诺·塔西合作,在罗马帕拉维奇尼·罗斯皮格里奥西宫(Palazzo Palavicini Rospigliosi)内装饰博物馆的拱顶。5月的一天,塔西拜访了詹蒂莱斯基一家,与阿特米西娅一人时强奸了她。另一名男子科西莫·库奥利(Cosimo Quorli)也参与了强奸案。
由于期望他们会结婚以恢复她的尊严和保障她的未来,阿特米西娅在强奸后开始与塔西发生性关系,但他违背了与阿特米西娅结婚的承诺。强奸案发生9个月后,当他得知阿特米西娅和塔西不打算结婚时,她的父亲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对塔西提出指控。奥拉齐奥还指控塔西从詹蒂莱斯基家偷了一幅朱迪思的画。这次事件的主要问题是塔西承认阿特米西娅的处女身份。如果阿特米西娅在塔西强奸她之前不是处女,根据当时法律,詹蒂莱斯基家族将无法提出指控。
在接下来的七个月的审判中,人们发现塔西计划谋杀他的妻子,与他的嫂子通奸,并计划偷一些奥拉齐奥的画。审判结束时,塔西被流放出罗马,尽管判决从未执行。在审判中,阿特米西娅被用指旋器折磨,目的是核实她的证词。
在12岁失去母亲后,阿特米西娅主要被男性包围。17岁时,奥拉齐奥将他们家楼上的公寓租给了一位名叫图齐亚(Tuzia)的女房客。阿特米西娅是图齐亚的朋友;然而,图齐亚允许阿戈斯蒂诺·塔西和科西莫·库奥利(Cosimo Quorli)多次到阿特米西娅的家中探访阿特米西娅。强奸发生的那天,阿特米西娅向图齐亚大声呼救,但图齐亚根本不理睬阿特米西娅,假装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图齐亚的背叛和在促进强奸方面的作用已被比作对妓女进行性剥削的同谋。
1976年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乌鸦巢发现的一幅名为《母与子》(Mother and Child )的画,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金蒂莱斯基所画。假定这是她的作品,这名婴儿被解释为间接提及她的强奸犯阿戈斯蒂诺·塔西,因为它可以追溯到1614年,也就是强奸案发生两年后。它描绘了一个坚强而痛苦的女人,揭示了她的痛苦和表达能力。
佛罗伦萨时期(1612-1620)
审判一个月后,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安排他的女儿与来自佛罗伦萨的谦逊艺术家皮兰托尼奥·斯蒂塔特西(Pierantonio Stiattesi)结婚。不久之后,这对夫妇搬到了佛罗伦萨。她在佛罗伦萨度过的六年对阿特米西娅的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涯都具有决定性意义。阿特米西娅成为了一位成功的宫廷画家,享有美第奇家族的赞助,并在城市的宫廷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生了五个孩子,尽管1620年离开佛罗伦萨时,只有两个还活着。她还开始了与佛罗伦萨贵族弗朗西斯科·玛丽亚·马林吉(Francesco Maria Maringhi)的激情关系。
作为一名艺术家,阿特米西娅在佛罗伦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是第一位进入绘画艺术学院的女性。她与她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艺术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Cristofano Allori,并赢得了有影响力人士的青睐和保护,首先是托斯卡纳大公爵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II de’Medici),尤其是洛林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of Lorraine)。从她在 1635 年写给这位科学家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她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相识似乎源于她在佛罗伦萨的岁月。 事实上,这可能激发了她在《倾斜寓言》中对罗盘的描绘。
她对佛罗伦萨宫廷文化的参与不仅为她提供了获得赞助者的机会,而且还扩大了她的教育和艺术接触。她学会了阅读和写作,熟悉了音乐和戏剧表演。这种艺术景观有助于阿特米西娅在她的绘画中描绘奢华的服饰:“阿特米西娅明白,在当代服饰中描绘圣经或神话人物……是宫廷生活景观的一个基本特征。”
1615年,她受到了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 the Younger,米开朗基罗较年轻的亲戚)的关注。他忙于建造布奥纳罗蒂之家(Casa Buonarroti)以庆祝他著名的叔公,他请阿特米西娅和其他佛罗伦萨艺术家,包括阿戈斯蒂诺·钱佩利(Agostino Ciampelli)、西吉斯蒙多·科卡帕尼(Sigismondo Coccapani)、乔万·巴蒂斯塔·吉多尼(Giovan Battista Guidoni)和Zanobi Rosi为天花板贡献一幅画。阿特米西娅当时处于妊娠晚期状态。每一位艺术家都被委托呈现一个与米开朗基罗有关的美德寓言,阿特米西娅被指定为《倾斜寓言》。在这种情况下,阿特米西娅的报酬是参与该系列的任何其他艺术家的三倍。她以一名手持指南针的裸体年轻女子的形式绘制了这幅图。她的画在二楼的画廊天花板上。据信,该形象与阿特米西娅相似。事实上,在她的几幅画中,阿特米西娅的充满活力的女主人公似乎都是自画像。
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作品包括《玛格达琳的皈依》(The Conversion of The Magdalene)、《琵琶手的自画像》和《朱迪思和她的女仆》。阿特米西娅画了《朱迪思斩首霍洛弗内斯(乌菲齐)》的第二个版本,现在位于佛罗伦萨乌菲齐画廊。在那不勒斯卡波迪蒙特博物馆展出了第一幅较小的《朱迪思斩首霍洛弗内斯》。阿特米西娅关于朱迪思斩首霍洛弗内斯的作品已知有六种版本存在。
在佛罗伦萨时,阿特米西娅和皮尔兰托尼奥有五个孩子。乔瓦尼·巴蒂斯塔、阿格诺拉和利萨贝拉已经活了一年多。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克里斯托法诺(Cristofano)在阿特米西娅回到罗马后去世,享年5岁。只有Prudentia能活到成年。Prudentia也被称为Palmira,这导致一些学者错误地得出结论,Artemisia有第六个孩子。Prudentia是以Artemisia的母亲的名字命名的,她在Artemisia 12岁时去世。据了解,阿特米西娅的女儿是一名画家,接受过母亲的培训,但对她的作品一无所知。
在佛罗伦萨期间,阿特米西娅和皮尔兰托尼奥(Pierantonio)有五个孩子。乔瓦尼·巴蒂斯塔(Giovanni Battista)、阿格诺拉(Agnola)和利萨贝拉(Lisabella) 都活了一年多。 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克里斯托法诺(Cristofano)在阿特米西娅回到罗马后五岁就去世了。 只有普鲁登蒂亚(Prudentia) 存活到成年。 普鲁登蒂亚也被称为帕尔米拉(Palmira),这导致一些学者错误地得出阿特米西娅有第六个孩子的结论。 普鲁登蒂亚得名于阿特米西娅的母亲,她在阿特米西娅12 岁时去世。众所周知,阿特米西娅的女儿是一名画家,并由她的母亲训练,尽管她的作品一无所知。
2011年,弗朗西斯科·索利纳斯(Francesco Solinas)发现了36封信的收藏,这些信的年代约为1616年至1620年,为佛罗伦萨詹蒂莱斯基家族的个人和经济生活增添了惊人的背景。他们表明,阿特米西娅与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玛丽亚·马林吉(Francesco Maria Maringhi)的富有的佛罗伦萨贵族有着激情的爱情。她的丈夫皮兰托尼奥·斯蒂塔特西(Pierantonio Stiattesi)非常清楚他们的关系,他在背后与马林吉保持着通信。 他容忍了,大概是因为马林吉是为这对夫妇提供经济支持的强大盟友。 然而,到 1620 年,这件事的谣言开始在佛罗伦萨宫廷中传播,再加上持续存在的法律和财务问题,这对夫妇搬到了罗马。
返回罗马(1620-1626/7)
与前十年一样,16世纪20年代初阿特米西娅的生活经历了持续的剧变。她的儿子克里斯托法诺(Cristofano)去世了。就在她到达罗马时,她的父亲奥拉齐奥前往热那亚。与情人马林吉的直接接触似乎减少了。到1623年,任何关于她丈夫的记载都从现存的文件中消失了。
她来到罗马,提供了与其他画家合作的机会,并从该市广泛的艺术收藏家网络中寻求赞助,阿特米西娅充分抓住了这些机会。一位艺术史学家在谈到这一时期时指出,“阿特米西娅在罗马的事业迅速腾飞,金钱问题也得到缓解”。然而,大规模的教皇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禁止的。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的长期教皇职位显示出对大型装饰作品和祭坛画的偏爱,以皮埃特罗·达·科尔托纳(Pietro da Cortona)的巴洛克风格为代表。詹蒂莱斯基在架上绘画方面的训练,以及对女性画家没有精力进行大规模绘画的怀疑,意味着乌尔班圈内雄心勃勃的赞助人委托了其他艺术家。
但罗马接待了各种各样的赞助人。西班牙的费尔南多·阿凡·德·里贝拉(Fernando Afan de Ribera),第三代阿尔卡拉·德洛斯·盖苏莱斯公爵( The 3rd Duke of Alcalá de los Gazules),她将自己画的抹大拉、大卫和基督祝福孩子们的画添加到了他的收藏中。在同一时期,她与卡西亚诺·达尔·波佐(Cassiano dal Pozzo)联系在一起,后者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达尔·波佐帮助与其他艺术家和赞助人建立了关系。她的声望提高了。1625年,来访的法国艺术家皮埃尔·杜蒙斯蒂尔二世(Pierre Dumonstier II)用黑色和红色粉笔画出了她的右手。
罗马赞助人的多样性也意味着风格的多样性。卡拉瓦乔的风格仍然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并使许多画家转向追随他的风格(所谓的卡拉瓦吉斯蒂),如Carlo Saraceni(1620年回到威尼斯)、Bartolomeo Manfredi和西蒙·沃伊特。詹蒂莱斯基和西蒙·沃伊特将继续保持职业关系,并将影响彼此的风格。沃伊特将继续完成一幅阿特米西娅的肖像画《阿特米西娅设计陵墓》。詹蒂莱斯基还与住在罗马的本特维厄尔(Bentveughels)画派(由佛兰芒和荷兰画家组成)进行了交流。博洛尼亚学派(Bolognese school,特别是在1621年至1623年格里高利十五世期间)也开始流行起来,她的《苏撒拿和长老们》经常与圭尔奇诺引入的风格联系在一起。
虽然有时很难确定她的绘画作品的年代,但可以将詹蒂莱斯基的某些作品归入这些年份,例如今天在博洛尼亚(她作为肖像画家的能力的罕见例子)的一幅冈法罗尼埃肖像画,以及今天在底特律艺术学院的《朱迪思和她的女仆与赫洛弗尼斯的头颅》。这幅底特律的画作以她对明暗对比和特内布里斯特(Tenebrism,阴暗主义,极光和黑暗的效果)的精通而闻名,杰拉德·范·洪索斯特和罗马的许多其他人都以这两种技术而闻名。
威尼斯三年(1626/7-1630)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很难了解16世纪20年代末詹蒂莱斯基的活动。然而,可以肯定的是,1626年至1627年间,她搬到了威尼斯,也许是为了寻求更丰厚的佣金。许多诗句和书信都是为了感谢她和她在威尼斯的作品而写的。对她在这段时间里的任务的了解是模糊的,但今天在里士满弗吉尼亚美术博物馆展出的《维纳斯和丘比特》,以及现在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的《以斯帖在亚哈随鲁王面前》,都证明了她吸收了威尼斯色彩主义的特点。
那不勒斯和英国时期(1630-1656)
1630年,阿特米西娅迁往那不勒斯,这是一个拥有众多作坊和艺术爱好者的城市,寻找新的、更赚钱的工作机会。十八世纪传记作家贝尔纳多·德多米尼奇( Bernardo de' Dominici)推测,阿特米西娅在她到达那不勒斯之前就已经在那不勒斯广为人知了。阿尔卡拉公爵费尔南多·恩里克斯·阿凡·德·里贝拉(Duke of Alcalá, Fernando Enriquez Afan de Ribera)可能邀请她到那不勒斯,她有三幅画:《悔改的抹大拉》、《上帝保佑孩子们》和《大卫和竖琴》(David and Goliath)。许多其他艺术家,包括卡拉瓦乔、安尼巴尔·卡拉奇和西蒙·沃伊特,一生中都在那不勒斯呆了一段时间。当时,胡塞佩·德·里贝拉、Massimo Stanzione和多梅尼基诺都在那里工作,后来,乔瓦尼·兰弗兰科(Giovanni Lanfranco)和其他许多人会蜂拥而至。卡波迪蒙特博物馆的《天使报喜》代表了那不勒斯首次出现的阿特米西娅。除了短暂的伦敦之行和其他一些旅行外,阿特米西娅在那不勒斯度过了她职业生涯的剩余时间。
克利奥帕特拉,1633-35年
1634年3月18日,星期六,旅行者布伦·雷姆斯(Bullen Reymes)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一群英国同胞一起访问阿特米西娅和她的女儿帕尔米拉(Palmira,“她也是画家”)。她与许多著名艺术家都有关系,其中包括Massimo Stanzione,据贝尔纳多·德多米尼奇(Bernardo de’Dominici)报道,她与斯坦齐安(Massimo Stanzione)展开了一场基于真正友谊和艺术相似性的艺术合作。阿特米西娅的作品影响了斯坦齐奥尼对颜色的使用,如1630年他对圣母的假设所示。德多米尼奇说,“斯坦齐奥尼从多梅尼基诺那里学会了如何创作史托里娅,但从阿特米西娅那里学会了他的色彩。”。
在那不勒斯,阿特米西娅第一次在一座大教堂里开始绘画。它们是献给波佐里的圣詹纳罗·内尔·安菲塔特罗·迪·波佐里(波佐里圆形剧场中的圣贾努里乌斯)。在她的第一个那不勒斯时期,她画了现在在马德里普拉多的《施洗者圣约翰的诞生》,以及今天在私人收藏中的《科丽斯卡与萨堤尔》。在这些画中,阿特米西娅再次展示了她适应这一时期的新奇事物和处理不同主题的能力,而不是通常的朱迪思、苏珊娜、芭丝谢芭和忏悔的玛格达琳,因为她已经为人所知。这些画中有许多是合作画。例如,拔示巴(Bathsheba)被认为是阿特米西娅(Artemisia)、Viviano Codazzi和加里尤洛(Gargiulo)的合作作品。
1638年,阿特米西娅在英国查理一世的宫廷与父亲会合,在那里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成为宫廷画家,并在格林威治为亨利埃塔·玛丽亚女王建造的女王官邸中接受了装饰天花板《和平与艺术的寓言》的重要工作。父亲和女儿又在一起工作了,尽管帮助父亲可能不是她去伦敦旅行的唯一原因:查尔斯一世邀请她去他的宫廷,无法拒绝。查理一世是一位热心的收藏家,他愿意为自己在艺术上的花费招致批评。阿特米西娅的名声可能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的收藏品中包括一幅极具启发性的绘画,《自画像作为绘画的寓言》(这是本文的主要图像),这并非巧合。
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于1639年突然去世。阿特米西娅在她父亲去世后有她自己的任务要完成,尽管没有已知的作品可以确定地分配给这一时期。众所周知,阿特米西娅于1642年离开英国,当时英国内战刚刚开始。关于她后来的行动,人们知之甚少。历史学家们知道,1649年,她再次来到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的唐·安东尼奥·鲁福(Don Antonio Ruffo)相对应,后者在第二个那不勒斯时期成为她的导师。最后一封写给她的导师的信是1650年的,信中明确表示她仍然非常活跃。
在她最后几年的活动中,她的作品很可能是委托创作的,并且在她的作品中遵循了女性的传统表现。
人们一度认为阿特米西娅死于1652年或1653年,然而,现代证据表明,1654年她仍然接受佣金,尽管她越来越依赖她的助手奥诺弗里奥·帕伦博(Onofrio Palumbo)。有人推测她死于1656年席卷那不勒斯的毁灭性瘟疫,几乎消灭了整整一代那不勒斯艺术家。
在《伯灵顿杂志》( The Burlington Magazin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艺术史学家吉安尼·帕皮(Gianni Papi)将她的《大卫与歌利亚的头》(David with the Head of Goliath)联系在一起,并于2020年在伦敦重新发现。
艺术重要性
意大利评论家罗伯托·隆吉(Roberto Longhi)的研究论文《詹蒂莱斯基父女》(Gentileschi, padre e figlia,1916年)将阿特米西娅描述为“意大利唯一了解绘画、着色、绘画和其他基本知识的女性”。隆吉还写到《朱迪思斩首霍洛弗内斯》(Judith Slaying Holofernes):“阿特米西娅·詹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的作品约有57部,94%(49部)的作品以女性为主角或与男性平等。”。这包括她的《杰尔和西塞拉》,《朱迪思和她的女仆》,以及《以斯帖在亚哈随鲁王面前》。这些角色故意缺乏刻板的“女性”特征——敏感、胆小和软弱,是勇敢、叛逆和强大的性格。一位十九世纪的评论家评论阿特米西娅的《抹大拉》,他说:“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一个女人的作品。画作大胆而明确,没有胆怯的迹象。”。沃德·比塞尔(Ward Bissell)认为,她很清楚男性是如何看待女性和女性艺术家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的作品在她职业生涯之初是如此大胆。
隆吉(Longhi)写道:
谁能想到,事实上,在一张如此坦率的床单上,会发生如此残忍和可怕的屠杀,但很自然地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女人!一个女人画了这一切……这里没有什么虐待狂的东西,相反,最令人震惊的是画家的冷漠,他甚至能够注意到,用暴力喷射的血液,可以用两滴来装饰中央喷射!我告诉你,难以置信!也请给夏特西夫人——阿特米西娅的夫妻名——选择剑柄的机会! 最后,你不认为朱迪斯的唯一目的是移开以避开可能弄脏她衣服的血吗?不管怎样,我们认为这是卡萨·金蒂莱斯基(Casa Gentileschi)的一件衣服,是1600年欧洲安东尼·凡·戴克之后最好的衣柜。"
女权主义者的研究增加了人们对阿特米西娅的兴趣,强调了她的强奸和随后的虐待,以及她在《圣经》中的女主人公绘画中的表现力,在这些画中,女性被解释为愿意表现她们对自身状况的反抗。2001年在罗马(以及之后在纽约)举办的“Orazio e Artemisia Gentileschi”展览目录中的一篇研究论文中,Judith W.Mann批评了女性主义对Artemisia的观点,发现在女性主义者对阿特米西娅绘画的解读中,旧的阿特米西娅性不道德的刻板印象已经被新的刻板印象所取代:
在不否认性别和性别可以为阿特米西娅艺术的研究提供有效的解释策略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想知道性别阅读的应用是否创造了过于狭隘的期望。作为加拉德(Garrard)专著的基础,雷蒙德·沃德·比塞尔(Raymond Ward Bissell)在其《理由》目录中以有限的方式重申了某些假设:阿特米西娅的全部创造力只出现在对坚强、自信的女性的描绘中,她不会参与传统的宗教形象,比如圣母与圣婴,或是一个服从报喜的圣母,她拒绝给出自己的个人解释,以符合她可能的男性客户的口味。这种刻板印象产生了双重限制效应,导致学者们质疑不符合模型的作品的归属,并对不符合模型的作品给予较低的重视。
由于阿特米西娅一次又一次地回归朱迪思和霍洛弗内斯等暴力题材,一些艺术史学家提出了一种压抑的复仇理论,但其他艺术史学家认为,她精明地利用强奸案审判中的名声,迎合了性指控的利基市场,女性主导的男性赞助人艺术。
最近的批评家们,从整个《詹蒂莱斯基》目录的艰难重建开始,试图对阿特米西娅的艺术生涯进行较少的还原性解读,将其置于画家所参与的不同艺术环境中。这样的解读使阿特米西娅恢复了作为一名艺术家的身份,她用个性和艺术品质的武器与对女画家的偏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能够在她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画家圈子里进行富有成效的自我介绍,包括一系列可能比她的绘画更丰富多样的绘画流派。
女性主义视角
女权主义者对青蒿的兴趣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女权主义艺术历史学家琳达·诺克林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剖析和分析。这篇文章探讨了“伟大艺术家”的定义,并认为压迫性的制度,而不是人才的缺乏,阻碍了女性在艺术和其他领域获得与男性同等水平的认可。诺克林说,对阿特米西娅和其他女性艺术家的研究“值得努力”,“增加我们对女性成就和总体艺术史的了解”根据道格拉斯·德鲁克(Douglas Druick)在伊芙·施特劳斯曼·普兰特(Eve Straussman Pflanzer)的《暴力与美德:阿特米西娅的朱迪思斩首霍洛弗内斯》中的前言,诺克林(Nochlin)的文章促使学者们更多地尝试“将女性艺术家融入艺术和文化史”
随着阿特米西娅及其作品开始在艺术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中获得新的关注,更多关于她的小说和传记文学被出版。1947年,评论家罗伯托·隆吉(Roberto Longhi)的妻子安娜·班蒂(Anna Banti)发表了一篇关于她生活的小说。这一说法受到文学评论家的好评,但也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尤其是劳拉·贝内代蒂(Laura Benedetti),因为她在历史准确性方面过于宽大,以便在作家和艺术家之间找到相似之处。1989年,女权主义艺术史学家玛丽·加勒德(Mary Garrard)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真实地描述阿特米西娅生活的书,书中描述了意大利巴洛克艺术中的女性英雄形象。随后,她在2001年出版了第二本较小的书,书名为《1622年左右的阿特米西娅:艺术身份的塑造与重塑》,探讨了艺术家的作品和身份。加拉德(Garrard)指出,对阿特米西娅作品的分析在“女性”之外缺乏重点和稳定的分类,尽管加拉德质疑女性是否是评判她的艺术的合法范畴。
阿特米西娅以其对女性力量团体中人物的刻画而闻名,例如她对朱迪思杀害霍洛弗内斯的版本。她还因参与强奸案而闻名,学者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认为,不幸的是,该案已成为反复出现的“解读艺术家作品的轴心”。波洛克认为,詹蒂莱斯基在流行文化中的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她的工作,不如说是由于她在遭受酷刑的强奸案审判中的持续关注而引起的轰动效应。波洛克对艺术家的戏剧性叙事画进行了反读,拒绝将朱迪思和霍洛弗内斯的照片视为对强奸和审判的回应。相反,波洛克指出,朱迪思和霍洛弗内斯的主题不是复仇主题,而是一个政治勇气的故事,事实上,是两名妇女在战争中进行了大胆的政治谋杀。波洛克试图将注意力从耸人听闻转向更深入地分析詹蒂莱斯基的绘画作品,尤其是死亡与失落,这表明她童年的丧亲之痛是她独特的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形象的来源。波洛克还认为,詹蒂莱斯基在17世纪的成功取决于她为赞助人创作的绘画作品,通常描绘他们选择的反映当代品味和时尚的主题。她旨在将詹蒂莱斯基的职业生涯置于其历史背景中,即对《圣经》或古典文学中女主人公的戏剧叙事的品味。
另一方面,美国教授卡米尔·帕格里亚(Camille Paglia)认为,现代女权主义者对阿特米西娅的关注是错误的,她的成就被夸大了:“阿特米西娅·詹蒂莱斯基只是一位优雅、能干的巴洛克风格画家,由男性创作。”尽管如此,据国家美术馆称,阿特米西娅“在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那不勒斯和伦敦为欧洲社会的最高阶层工作,包括托斯卡纳大公爵和西班牙菲利普四世”。
女权主义文学倾向于围绕阿特米西娅的强奸事件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把她描绘成一个受过创伤但高贵的幸存者,由于她的经历,她的作品以性和暴力为特征。劳拉·贝内代蒂(Laura Benedetti)的一篇文献综述《重建阿特米西娅:二十世纪一位女艺术家的形象》得出结论,阿特米西娅的作品往往是根据当代问题和作者的个人偏见来解读的。例如,女权主义者学者将阿特米西娅提升为女权主义者偶像的地位,贝内代蒂将这归功于阿特米西娅画出的令人敬畏的女性,以及她作为一名艺术家在男性主导的领域取得的成功,同时她也是一名单身母亲。埃琳娜·西莱蒂(Elena Ciletti)写道,“阿特米西娅的案子关系重大,特别是对女权主义者而言,因为我们在为女性争取正义的过程中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在,从思想上还是政治上。”
女权主义者学者认为,阿特米西娅希望站出来反对女性顺从的刻板印象。这一象征意义的一个例子出现在1630年至1635年间创作的《科丽斯卡与萨堤尔》中。在这幅画中,一个仙女从一个萨提尔身边跑开了。萨提尔试图抓住仙女的头发,但她的头发是假发。在这里,阿特米西娅描绘了仙女相当聪明,积极抵抗萨提尔的攻击。
她那个时代的其他女画家
对于十七世纪初的一位女性来说,阿特米西娅作为一名画家代表了一个不寻常和艰难的选择,但不是一个例外。阿特米西娅意识到“她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的地位以及目前女性与艺术关系的表现。”这一点在她的寓言性自画像《自画像作为绘画的寓言》中很明显,这幅自画像将阿特米西娅作为缪斯女神、“艺术的象征性体现”和专业艺术家展现出来。
在阿特米西娅艺术之前,从16世纪末到16世纪初,其他女性画家都有着成功的职业生涯,包括Sofonisba Anguissola。后来,Fede Galizia画了静物画和《朱迪斯斩首赫洛弗尼斯》。
意大利巴洛克画家Elisabetta Sirani是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女性艺术家。西拉尼的寓言画《自画像作为绘画的寓言》与阿特米西娅的作品有着共同的配色方案。她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很受欢迎,但她被认可了。
其他女画家也在阿特米西娅还活着的时候开始了她们的职业生涯。从它们的艺术价值来看,隆吉(Longhi)关于阿特米西娅是“意大利唯一一位了解绘画的女性”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阿特米西娅仍然是最受尊敬的女性艺术家之一,她在伟大的巴洛克艺术家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在流行文化中
在电视上
《皇冠》(第三季第1集)中提到了阿特米西娅·詹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的一幅无名画。菲利普亲王看到这幅画,问安东尼·布朗特爵士作者是谁,布朗特回答说“阿特米西娅”,菲利普说“从未听说过他”“她,先生,”布朗特纠正了他。
在电影院
阿格尼丝·梅雷特(Agnès Merlet)拍摄的电影《阿特米西娅》(1997)讲述了阿特米西娅成为职业艺术家的故事、她与塔西的关系以及审判。然而,梅雷特为塔西的强奸开脱,不仅通过将他们的性描写为爱和自愿的(这在电影发行时是有争议的),而且还通过两个非历史性的捏造:阿特米西娅否认酷刑下的强奸,而塔西谎称强奸以停止对阿特米西娅的折磨。
约旦河拍摄的纪录片《阿特米西娅:战士画家》于2020年上映。
网上
2020年7月8日,谷歌用谷歌涂鸦庆祝阿特米西娅427岁生日。
生卒日期: 1593年7月8日 - 大约1652年
国籍:意大利
阿特米西娅·詹蒂莱斯基的全部作品(76)
阿特米西娅·詹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Artemisia Lomi),又译为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意大利巴洛克画家。詹蒂莱斯基被认为是17世纪最有成就的艺术家之一,最初以卡拉瓦乔的风格工作。她十五岁时就开始从事专业工作。在一个女性几乎没有机会接受艺术培训或从事专业艺术家工作的时代,真蒂莱斯基是第一位成为佛罗伦萨“艺术学院”成员的女性,她拥有国际客户。
詹蒂莱斯基的许多画作都描绘了神话、寓言和圣经中的女性,包括受害者、自杀者和战士。她的一些最著名的主题是《苏撒拿与长老》、《朱迪思斩首霍洛弗内斯(乌菲齐)》,以及《朱迪思和她的女仆与赫洛弗尼斯的头颅》。
詹蒂莱斯基以能够以极大的自然主义描绘女性形象而闻名,并以其处理色彩以表达维度和戏剧性的技巧而闻名。
阿戈斯蒂诺·塔西(Agostino Tassi)年轻时强奸她的故事以及她参与对强奸犯的审判,使她作为艺术家的成就长期蒙上阴影。多年来,詹蒂莱斯基一直被视为一个好奇的人,但她的生活和艺术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受到了学者们的重新审视。她现在被认为是她这一代人中最进步、最富有表现力的画家之一,在伦敦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等国际知名美术机构举办的大型展览充分证明了她的才华。
传记
早年生活
阿特米西娅(Artemisia Lomi Gentileschi)于1593年7月8日出生于罗马,尽管她的出生证明表明她出生于1590年。她是普鲁登齐亚·迪奥塔维亚诺·蒙托尼(Prudenzia di Ottaviano Montoni)和托斯卡纳画家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的长女。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是来自比萨的画家。到达罗马后,他的绘画达到了表现力的巅峰,灵感来自卡拉瓦乔的创新,他从中养成了画真实模特的习惯,没有将模型理想化或美化,事实上,也没有将其改造成一部强有力的现实主义戏剧。1605年,小阿特米西娅在卢西纳圣洛伦佐教堂出生两天后接受洗礼,成为母亲的孤儿。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她开始接触绘画:阿特米西娅是在她父亲的工作室里被介绍到绘画的,表现出比与她一起工作的兄弟们更多的热情和才华。她学会了绘画,如何混合颜色,以及如何作画。到1612年,当她还不到19岁时,她的父亲就可以夸耀她堪称楷模的才华,声称在她已经从事了三年的绘画职业中,她是无与伦比的。
在那个时期,她父亲的风格受到卡拉瓦乔的启发,所以她的风格也深受他的影响。然而,阿特米西娅对主题的态度与她父亲不同。她的画很自然。奥拉齐奥的是理想化的。与此同时,阿特米西娅必须克服“传统态度和心理屈服于这种洗脑和对她明显天赋的嫉妒”。通过这样做,她的工作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和认可。
她现存的最早作品是17岁时的《苏撒拿与长老》。这幅画描绘了《圣经》中苏珊娜的故事。这幅画展示了阿特米西娅是如何吸收卡拉瓦乔的现实主义和效果的,而不是漠视安尼巴尔·卡拉奇的古典主义和巴洛克风格的博洛尼亚学派( Bolognese School)。
阿戈斯蒂诺·塔西强奸案
1611年,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与阿戈斯蒂诺·塔西合作,在罗马帕拉维奇尼·罗斯皮格里奥西宫(Palazzo Palavicini Rospigliosi)内装饰博物馆的拱顶。5月的一天,塔西拜访了詹蒂莱斯基一家,与阿特米西娅一人时强奸了她。另一名男子科西莫·库奥利(Cosimo Quorli)也参与了强奸案。
由于期望他们会结婚以恢复她的尊严和保障她的未来,阿特米西娅在强奸后开始与塔西发生性关系,但他违背了与阿特米西娅结婚的承诺。强奸案发生9个月后,当他得知阿特米西娅和塔西不打算结婚时,她的父亲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对塔西提出指控。奥拉齐奥还指控塔西从詹蒂莱斯基家偷了一幅朱迪思的画。这次事件的主要问题是塔西承认阿特米西娅的处女身份。如果阿特米西娅在塔西强奸她之前不是处女,根据当时法律,詹蒂莱斯基家族将无法提出指控。
在接下来的七个月的审判中,人们发现塔西计划谋杀他的妻子,与他的嫂子通奸,并计划偷一些奥拉齐奥的画。审判结束时,塔西被流放出罗马,尽管判决从未执行。在审判中,阿特米西娅被用指旋器折磨,目的是核实她的证词。
在12岁失去母亲后,阿特米西娅主要被男性包围。17岁时,奥拉齐奥将他们家楼上的公寓租给了一位名叫图齐亚(Tuzia)的女房客。阿特米西娅是图齐亚的朋友;然而,图齐亚允许阿戈斯蒂诺·塔西和科西莫·库奥利(Cosimo Quorli)多次到阿特米西娅的家中探访阿特米西娅。强奸发生的那天,阿特米西娅向图齐亚大声呼救,但图齐亚根本不理睬阿特米西娅,假装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图齐亚的背叛和在促进强奸方面的作用已被比作对妓女进行性剥削的同谋。
1976年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乌鸦巢发现的一幅名为《母与子》(Mother and Child )的画,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金蒂莱斯基所画。假定这是她的作品,这名婴儿被解释为间接提及她的强奸犯阿戈斯蒂诺·塔西,因为它可以追溯到1614年,也就是强奸案发生两年后。它描绘了一个坚强而痛苦的女人,揭示了她的痛苦和表达能力。
佛罗伦萨时期(1612-1620)
审判一个月后,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安排他的女儿与来自佛罗伦萨的谦逊艺术家皮兰托尼奥·斯蒂塔特西(Pierantonio Stiattesi)结婚。不久之后,这对夫妇搬到了佛罗伦萨。她在佛罗伦萨度过的六年对阿特米西娅的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涯都具有决定性意义。阿特米西娅成为了一位成功的宫廷画家,享有美第奇家族的赞助,并在城市的宫廷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生了五个孩子,尽管1620年离开佛罗伦萨时,只有两个还活着。她还开始了与佛罗伦萨贵族弗朗西斯科·玛丽亚·马林吉(Francesco Maria Maringhi)的激情关系。
作为一名艺术家,阿特米西娅在佛罗伦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是第一位进入绘画艺术学院的女性。她与她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艺术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Cristofano Allori,并赢得了有影响力人士的青睐和保护,首先是托斯卡纳大公爵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II de’Medici),尤其是洛林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of Lorraine)。从她在 1635 年写给这位科学家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她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相识似乎源于她在佛罗伦萨的岁月。 事实上,这可能激发了她在《倾斜寓言》中对罗盘的描绘。
她对佛罗伦萨宫廷文化的参与不仅为她提供了获得赞助者的机会,而且还扩大了她的教育和艺术接触。她学会了阅读和写作,熟悉了音乐和戏剧表演。这种艺术景观有助于阿特米西娅在她的绘画中描绘奢华的服饰:“阿特米西娅明白,在当代服饰中描绘圣经或神话人物……是宫廷生活景观的一个基本特征。”
1615年,她受到了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 the Younger,米开朗基罗较年轻的亲戚)的关注。他忙于建造布奥纳罗蒂之家(Casa Buonarroti)以庆祝他著名的叔公,他请阿特米西娅和其他佛罗伦萨艺术家,包括阿戈斯蒂诺·钱佩利(Agostino Ciampelli)、西吉斯蒙多·科卡帕尼(Sigismondo Coccapani)、乔万·巴蒂斯塔·吉多尼(Giovan Battista Guidoni)和Zanobi Rosi为天花板贡献一幅画。阿特米西娅当时处于妊娠晚期状态。每一位艺术家都被委托呈现一个与米开朗基罗有关的美德寓言,阿特米西娅被指定为《倾斜寓言》。在这种情况下,阿特米西娅的报酬是参与该系列的任何其他艺术家的三倍。她以一名手持指南针的裸体年轻女子的形式绘制了这幅图。她的画在二楼的画廊天花板上。据信,该形象与阿特米西娅相似。事实上,在她的几幅画中,阿特米西娅的充满活力的女主人公似乎都是自画像。
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作品包括《玛格达琳的皈依》(The Conversion of The Magdalene)、《琵琶手的自画像》和《朱迪思和她的女仆》。阿特米西娅画了《朱迪思斩首霍洛弗内斯(乌菲齐)》的第二个版本,现在位于佛罗伦萨乌菲齐画廊。在那不勒斯卡波迪蒙特博物馆展出了第一幅较小的《朱迪思斩首霍洛弗内斯》。阿特米西娅关于朱迪思斩首霍洛弗内斯的作品已知有六种版本存在。
在佛罗伦萨时,阿特米西娅和皮尔兰托尼奥有五个孩子。乔瓦尼·巴蒂斯塔、阿格诺拉和利萨贝拉已经活了一年多。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克里斯托法诺(Cristofano)在阿特米西娅回到罗马后去世,享年5岁。只有Prudentia能活到成年。Prudentia也被称为Palmira,这导致一些学者错误地得出结论,Artemisia有第六个孩子。Prudentia是以Artemisia的母亲的名字命名的,她在Artemisia 12岁时去世。据了解,阿特米西娅的女儿是一名画家,接受过母亲的培训,但对她的作品一无所知。
在佛罗伦萨期间,阿特米西娅和皮尔兰托尼奥(Pierantonio)有五个孩子。乔瓦尼·巴蒂斯塔(Giovanni Battista)、阿格诺拉(Agnola)和利萨贝拉(Lisabella) 都活了一年多。 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克里斯托法诺(Cristofano)在阿特米西娅回到罗马后五岁就去世了。 只有普鲁登蒂亚(Prudentia) 存活到成年。 普鲁登蒂亚也被称为帕尔米拉(Palmira),这导致一些学者错误地得出阿特米西娅有第六个孩子的结论。 普鲁登蒂亚得名于阿特米西娅的母亲,她在阿特米西娅12 岁时去世。众所周知,阿特米西娅的女儿是一名画家,并由她的母亲训练,尽管她的作品一无所知。
2011年,弗朗西斯科·索利纳斯(Francesco Solinas)发现了36封信的收藏,这些信的年代约为1616年至1620年,为佛罗伦萨詹蒂莱斯基家族的个人和经济生活增添了惊人的背景。他们表明,阿特米西娅与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玛丽亚·马林吉(Francesco Maria Maringhi)的富有的佛罗伦萨贵族有着激情的爱情。她的丈夫皮兰托尼奥·斯蒂塔特西(Pierantonio Stiattesi)非常清楚他们的关系,他在背后与马林吉保持着通信。 他容忍了,大概是因为马林吉是为这对夫妇提供经济支持的强大盟友。 然而,到 1620 年,这件事的谣言开始在佛罗伦萨宫廷中传播,再加上持续存在的法律和财务问题,这对夫妇搬到了罗马。
返回罗马(1620-1626/7)
与前十年一样,16世纪20年代初阿特米西娅的生活经历了持续的剧变。她的儿子克里斯托法诺(Cristofano)去世了。就在她到达罗马时,她的父亲奥拉齐奥前往热那亚。与情人马林吉的直接接触似乎减少了。到1623年,任何关于她丈夫的记载都从现存的文件中消失了。
她来到罗马,提供了与其他画家合作的机会,并从该市广泛的艺术收藏家网络中寻求赞助,阿特米西娅充分抓住了这些机会。一位艺术史学家在谈到这一时期时指出,“阿特米西娅在罗马的事业迅速腾飞,金钱问题也得到缓解”。然而,大规模的教皇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禁止的。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的长期教皇职位显示出对大型装饰作品和祭坛画的偏爱,以皮埃特罗·达·科尔托纳(Pietro da Cortona)的巴洛克风格为代表。詹蒂莱斯基在架上绘画方面的训练,以及对女性画家没有精力进行大规模绘画的怀疑,意味着乌尔班圈内雄心勃勃的赞助人委托了其他艺术家。
但罗马接待了各种各样的赞助人。西班牙的费尔南多·阿凡·德·里贝拉(Fernando Afan de Ribera),第三代阿尔卡拉·德洛斯·盖苏莱斯公爵( The 3rd Duke of Alcalá de los Gazules),她将自己画的抹大拉、大卫和基督祝福孩子们的画添加到了他的收藏中。在同一时期,她与卡西亚诺·达尔·波佐(Cassiano dal Pozzo)联系在一起,后者是一位人文主义者、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达尔·波佐帮助与其他艺术家和赞助人建立了关系。她的声望提高了。1625年,来访的法国艺术家皮埃尔·杜蒙斯蒂尔二世(Pierre Dumonstier II)用黑色和红色粉笔画出了她的右手。
罗马赞助人的多样性也意味着风格的多样性。卡拉瓦乔的风格仍然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并使许多画家转向追随他的风格(所谓的卡拉瓦吉斯蒂),如Carlo Saraceni(1620年回到威尼斯)、Bartolomeo Manfredi和西蒙·沃伊特。詹蒂莱斯基和西蒙·沃伊特将继续保持职业关系,并将影响彼此的风格。沃伊特将继续完成一幅阿特米西娅的肖像画《阿特米西娅设计陵墓》。詹蒂莱斯基还与住在罗马的本特维厄尔(Bentveughels)画派(由佛兰芒和荷兰画家组成)进行了交流。博洛尼亚学派(Bolognese school,特别是在1621年至1623年格里高利十五世期间)也开始流行起来,她的《苏撒拿和长老们》经常与圭尔奇诺引入的风格联系在一起。
虽然有时很难确定她的绘画作品的年代,但可以将詹蒂莱斯基的某些作品归入这些年份,例如今天在博洛尼亚(她作为肖像画家的能力的罕见例子)的一幅冈法罗尼埃肖像画,以及今天在底特律艺术学院的《朱迪思和她的女仆与赫洛弗尼斯的头颅》。这幅底特律的画作以她对明暗对比和特内布里斯特(Tenebrism,阴暗主义,极光和黑暗的效果)的精通而闻名,杰拉德·范·洪索斯特和罗马的许多其他人都以这两种技术而闻名。
威尼斯三年(1626/7-1630)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很难了解16世纪20年代末詹蒂莱斯基的活动。然而,可以肯定的是,1626年至1627年间,她搬到了威尼斯,也许是为了寻求更丰厚的佣金。许多诗句和书信都是为了感谢她和她在威尼斯的作品而写的。对她在这段时间里的任务的了解是模糊的,但今天在里士满弗吉尼亚美术博物馆展出的《维纳斯和丘比特》,以及现在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的《以斯帖在亚哈随鲁王面前》,都证明了她吸收了威尼斯色彩主义的特点。
那不勒斯和英国时期(1630-1656)
1630年,阿特米西娅迁往那不勒斯,这是一个拥有众多作坊和艺术爱好者的城市,寻找新的、更赚钱的工作机会。十八世纪传记作家贝尔纳多·德多米尼奇( Bernardo de' Dominici)推测,阿特米西娅在她到达那不勒斯之前就已经在那不勒斯广为人知了。阿尔卡拉公爵费尔南多·恩里克斯·阿凡·德·里贝拉(Duke of Alcalá, Fernando Enriquez Afan de Ribera)可能邀请她到那不勒斯,她有三幅画:《悔改的抹大拉》、《上帝保佑孩子们》和《大卫和竖琴》(David and Goliath)。许多其他艺术家,包括卡拉瓦乔、安尼巴尔·卡拉奇和西蒙·沃伊特,一生中都在那不勒斯呆了一段时间。当时,胡塞佩·德·里贝拉、Massimo Stanzione和多梅尼基诺都在那里工作,后来,乔瓦尼·兰弗兰科(Giovanni Lanfranco)和其他许多人会蜂拥而至。卡波迪蒙特博物馆的《天使报喜》代表了那不勒斯首次出现的阿特米西娅。除了短暂的伦敦之行和其他一些旅行外,阿特米西娅在那不勒斯度过了她职业生涯的剩余时间。
克利奥帕特拉,1633-35年
1634年3月18日,星期六,旅行者布伦·雷姆斯(Bullen Reymes)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一群英国同胞一起访问阿特米西娅和她的女儿帕尔米拉(Palmira,“她也是画家”)。她与许多著名艺术家都有关系,其中包括Massimo Stanzione,据贝尔纳多·德多米尼奇(Bernardo de’Dominici)报道,她与斯坦齐安(Massimo Stanzione)展开了一场基于真正友谊和艺术相似性的艺术合作。阿特米西娅的作品影响了斯坦齐奥尼对颜色的使用,如1630年他对圣母的假设所示。德多米尼奇说,“斯坦齐奥尼从多梅尼基诺那里学会了如何创作史托里娅,但从阿特米西娅那里学会了他的色彩。”。
在那不勒斯,阿特米西娅第一次在一座大教堂里开始绘画。它们是献给波佐里的圣詹纳罗·内尔·安菲塔特罗·迪·波佐里(波佐里圆形剧场中的圣贾努里乌斯)。在她的第一个那不勒斯时期,她画了现在在马德里普拉多的《施洗者圣约翰的诞生》,以及今天在私人收藏中的《科丽斯卡与萨堤尔》。在这些画中,阿特米西娅再次展示了她适应这一时期的新奇事物和处理不同主题的能力,而不是通常的朱迪思、苏珊娜、芭丝谢芭和忏悔的玛格达琳,因为她已经为人所知。这些画中有许多是合作画。例如,拔示巴(Bathsheba)被认为是阿特米西娅(Artemisia)、Viviano Codazzi和加里尤洛(Gargiulo)的合作作品。
1638年,阿特米西娅在英国查理一世的宫廷与父亲会合,在那里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成为宫廷画家,并在格林威治为亨利埃塔·玛丽亚女王建造的女王官邸中接受了装饰天花板《和平与艺术的寓言》的重要工作。父亲和女儿又在一起工作了,尽管帮助父亲可能不是她去伦敦旅行的唯一原因:查尔斯一世邀请她去他的宫廷,无法拒绝。查理一世是一位热心的收藏家,他愿意为自己在艺术上的花费招致批评。阿特米西娅的名声可能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的收藏品中包括一幅极具启发性的绘画,《自画像作为绘画的寓言》(这是本文的主要图像),这并非巧合。
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于1639年突然去世。阿特米西娅在她父亲去世后有她自己的任务要完成,尽管没有已知的作品可以确定地分配给这一时期。众所周知,阿特米西娅于1642年离开英国,当时英国内战刚刚开始。关于她后来的行动,人们知之甚少。历史学家们知道,1649年,她再次来到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的唐·安东尼奥·鲁福(Don Antonio Ruffo)相对应,后者在第二个那不勒斯时期成为她的导师。最后一封写给她的导师的信是1650年的,信中明确表示她仍然非常活跃。
在她最后几年的活动中,她的作品很可能是委托创作的,并且在她的作品中遵循了女性的传统表现。
人们一度认为阿特米西娅死于1652年或1653年,然而,现代证据表明,1654年她仍然接受佣金,尽管她越来越依赖她的助手奥诺弗里奥·帕伦博(Onofrio Palumbo)。有人推测她死于1656年席卷那不勒斯的毁灭性瘟疫,几乎消灭了整整一代那不勒斯艺术家。
在《伯灵顿杂志》( The Burlington Magazin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艺术史学家吉安尼·帕皮(Gianni Papi)将她的《大卫与歌利亚的头》(David with the Head of Goliath)联系在一起,并于2020年在伦敦重新发现。
艺术重要性
意大利评论家罗伯托·隆吉(Roberto Longhi)的研究论文《詹蒂莱斯基父女》(Gentileschi, padre e figlia,1916年)将阿特米西娅描述为“意大利唯一了解绘画、着色、绘画和其他基本知识的女性”。隆吉还写到《朱迪思斩首霍洛弗内斯》(Judith Slaying Holofernes):“阿特米西娅·詹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的作品约有57部,94%(49部)的作品以女性为主角或与男性平等。”。这包括她的《杰尔和西塞拉》,《朱迪思和她的女仆》,以及《以斯帖在亚哈随鲁王面前》。这些角色故意缺乏刻板的“女性”特征——敏感、胆小和软弱,是勇敢、叛逆和强大的性格。一位十九世纪的评论家评论阿特米西娅的《抹大拉》,他说:“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一个女人的作品。画作大胆而明确,没有胆怯的迹象。”。沃德·比塞尔(Ward Bissell)认为,她很清楚男性是如何看待女性和女性艺术家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的作品在她职业生涯之初是如此大胆。
隆吉(Longhi)写道:
谁能想到,事实上,在一张如此坦率的床单上,会发生如此残忍和可怕的屠杀,但很自然地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女人!一个女人画了这一切……这里没有什么虐待狂的东西,相反,最令人震惊的是画家的冷漠,他甚至能够注意到,用暴力喷射的血液,可以用两滴来装饰中央喷射!我告诉你,难以置信!也请给夏特西夫人——阿特米西娅的夫妻名——选择剑柄的机会! 最后,你不认为朱迪斯的唯一目的是移开以避开可能弄脏她衣服的血吗?不管怎样,我们认为这是卡萨·金蒂莱斯基(Casa Gentileschi)的一件衣服,是1600年欧洲安东尼·凡·戴克之后最好的衣柜。"
女权主义者的研究增加了人们对阿特米西娅的兴趣,强调了她的强奸和随后的虐待,以及她在《圣经》中的女主人公绘画中的表现力,在这些画中,女性被解释为愿意表现她们对自身状况的反抗。2001年在罗马(以及之后在纽约)举办的“Orazio e Artemisia Gentileschi”展览目录中的一篇研究论文中,Judith W.Mann批评了女性主义对Artemisia的观点,发现在女性主义者对阿特米西娅绘画的解读中,旧的阿特米西娅性不道德的刻板印象已经被新的刻板印象所取代:
在不否认性别和性别可以为阿特米西娅艺术的研究提供有效的解释策略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想知道性别阅读的应用是否创造了过于狭隘的期望。作为加拉德(Garrard)专著的基础,雷蒙德·沃德·比塞尔(Raymond Ward Bissell)在其《理由》目录中以有限的方式重申了某些假设:阿特米西娅的全部创造力只出现在对坚强、自信的女性的描绘中,她不会参与传统的宗教形象,比如圣母与圣婴,或是一个服从报喜的圣母,她拒绝给出自己的个人解释,以符合她可能的男性客户的口味。这种刻板印象产生了双重限制效应,导致学者们质疑不符合模型的作品的归属,并对不符合模型的作品给予较低的重视。
由于阿特米西娅一次又一次地回归朱迪思和霍洛弗内斯等暴力题材,一些艺术史学家提出了一种压抑的复仇理论,但其他艺术史学家认为,她精明地利用强奸案审判中的名声,迎合了性指控的利基市场,女性主导的男性赞助人艺术。
最近的批评家们,从整个《詹蒂莱斯基》目录的艰难重建开始,试图对阿特米西娅的艺术生涯进行较少的还原性解读,将其置于画家所参与的不同艺术环境中。这样的解读使阿特米西娅恢复了作为一名艺术家的身份,她用个性和艺术品质的武器与对女画家的偏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能够在她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画家圈子里进行富有成效的自我介绍,包括一系列可能比她的绘画更丰富多样的绘画流派。
女性主义视角
女权主义者对青蒿的兴趣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女权主义艺术历史学家琳达·诺克林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剖析和分析。这篇文章探讨了“伟大艺术家”的定义,并认为压迫性的制度,而不是人才的缺乏,阻碍了女性在艺术和其他领域获得与男性同等水平的认可。诺克林说,对阿特米西娅和其他女性艺术家的研究“值得努力”,“增加我们对女性成就和总体艺术史的了解”根据道格拉斯·德鲁克(Douglas Druick)在伊芙·施特劳斯曼·普兰特(Eve Straussman Pflanzer)的《暴力与美德:阿特米西娅的朱迪思斩首霍洛弗内斯》中的前言,诺克林(Nochlin)的文章促使学者们更多地尝试“将女性艺术家融入艺术和文化史”
随着阿特米西娅及其作品开始在艺术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中获得新的关注,更多关于她的小说和传记文学被出版。1947年,评论家罗伯托·隆吉(Roberto Longhi)的妻子安娜·班蒂(Anna Banti)发表了一篇关于她生活的小说。这一说法受到文学评论家的好评,但也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尤其是劳拉·贝内代蒂(Laura Benedetti),因为她在历史准确性方面过于宽大,以便在作家和艺术家之间找到相似之处。1989年,女权主义艺术史学家玛丽·加勒德(Mary Garrard)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真实地描述阿特米西娅生活的书,书中描述了意大利巴洛克艺术中的女性英雄形象。随后,她在2001年出版了第二本较小的书,书名为《1622年左右的阿特米西娅:艺术身份的塑造与重塑》,探讨了艺术家的作品和身份。加拉德(Garrard)指出,对阿特米西娅作品的分析在“女性”之外缺乏重点和稳定的分类,尽管加拉德质疑女性是否是评判她的艺术的合法范畴。
阿特米西娅以其对女性力量团体中人物的刻画而闻名,例如她对朱迪思杀害霍洛弗内斯的版本。她还因参与强奸案而闻名,学者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认为,不幸的是,该案已成为反复出现的“解读艺术家作品的轴心”。波洛克认为,詹蒂莱斯基在流行文化中的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她的工作,不如说是由于她在遭受酷刑的强奸案审判中的持续关注而引起的轰动效应。波洛克对艺术家的戏剧性叙事画进行了反读,拒绝将朱迪思和霍洛弗内斯的照片视为对强奸和审判的回应。相反,波洛克指出,朱迪思和霍洛弗内斯的主题不是复仇主题,而是一个政治勇气的故事,事实上,是两名妇女在战争中进行了大胆的政治谋杀。波洛克试图将注意力从耸人听闻转向更深入地分析詹蒂莱斯基的绘画作品,尤其是死亡与失落,这表明她童年的丧亲之痛是她独特的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形象的来源。波洛克还认为,詹蒂莱斯基在17世纪的成功取决于她为赞助人创作的绘画作品,通常描绘他们选择的反映当代品味和时尚的主题。她旨在将詹蒂莱斯基的职业生涯置于其历史背景中,即对《圣经》或古典文学中女主人公的戏剧叙事的品味。
另一方面,美国教授卡米尔·帕格里亚(Camille Paglia)认为,现代女权主义者对阿特米西娅的关注是错误的,她的成就被夸大了:“阿特米西娅·詹蒂莱斯基只是一位优雅、能干的巴洛克风格画家,由男性创作。”尽管如此,据国家美术馆称,阿特米西娅“在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那不勒斯和伦敦为欧洲社会的最高阶层工作,包括托斯卡纳大公爵和西班牙菲利普四世”。
女权主义文学倾向于围绕阿特米西娅的强奸事件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把她描绘成一个受过创伤但高贵的幸存者,由于她的经历,她的作品以性和暴力为特征。劳拉·贝内代蒂(Laura Benedetti)的一篇文献综述《重建阿特米西娅:二十世纪一位女艺术家的形象》得出结论,阿特米西娅的作品往往是根据当代问题和作者的个人偏见来解读的。例如,女权主义者学者将阿特米西娅提升为女权主义者偶像的地位,贝内代蒂将这归功于阿特米西娅画出的令人敬畏的女性,以及她作为一名艺术家在男性主导的领域取得的成功,同时她也是一名单身母亲。埃琳娜·西莱蒂(Elena Ciletti)写道,“阿特米西娅的案子关系重大,特别是对女权主义者而言,因为我们在为女性争取正义的过程中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在,从思想上还是政治上。”
女权主义者学者认为,阿特米西娅希望站出来反对女性顺从的刻板印象。这一象征意义的一个例子出现在1630年至1635年间创作的《科丽斯卡与萨堤尔》中。在这幅画中,一个仙女从一个萨提尔身边跑开了。萨提尔试图抓住仙女的头发,但她的头发是假发。在这里,阿特米西娅描绘了仙女相当聪明,积极抵抗萨提尔的攻击。
她那个时代的其他女画家
对于十七世纪初的一位女性来说,阿特米西娅作为一名画家代表了一个不寻常和艰难的选择,但不是一个例外。阿特米西娅意识到“她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的地位以及目前女性与艺术关系的表现。”这一点在她的寓言性自画像《自画像作为绘画的寓言》中很明显,这幅自画像将阿特米西娅作为缪斯女神、“艺术的象征性体现”和专业艺术家展现出来。
在阿特米西娅艺术之前,从16世纪末到16世纪初,其他女性画家都有着成功的职业生涯,包括Sofonisba Anguissola。后来,Fede Galizia画了静物画和《朱迪斯斩首赫洛弗尼斯》。
意大利巴洛克画家Elisabetta Sirani是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女性艺术家。西拉尼的寓言画《自画像作为绘画的寓言》与阿特米西娅的作品有着共同的配色方案。她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很受欢迎,但她被认可了。
其他女画家也在阿特米西娅还活着的时候开始了她们的职业生涯。从它们的艺术价值来看,隆吉(Longhi)关于阿特米西娅是“意大利唯一一位了解绘画的女性”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毫无疑问,阿特米西娅仍然是最受尊敬的女性艺术家之一,她在伟大的巴洛克艺术家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在流行文化中
在电视上
《皇冠》(第三季第1集)中提到了阿特米西娅·詹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的一幅无名画。菲利普亲王看到这幅画,问安东尼·布朗特爵士作者是谁,布朗特回答说“阿特米西娅”,菲利普说“从未听说过他”“她,先生,”布朗特纠正了他。
在电影院
阿格尼丝·梅雷特(Agnès Merlet)拍摄的电影《阿特米西娅》(1997)讲述了阿特米西娅成为职业艺术家的故事、她与塔西的关系以及审判。然而,梅雷特为塔西的强奸开脱,不仅通过将他们的性描写为爱和自愿的(这在电影发行时是有争议的),而且还通过两个非历史性的捏造:阿特米西娅否认酷刑下的强奸,而塔西谎称强奸以停止对阿特米西娅的折磨。
约旦河拍摄的纪录片《阿特米西娅:战士画家》于2020年上映。
网上
2020年7月8日,谷歌用谷歌涂鸦庆祝阿特米西娅427岁生日。